2019年3月26日,欧盟议会投票通过了新一轮数字单一市场(Digital Single Market)版权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三章(Article 13)对于线上图像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再创作等行为做出了比当前更为紧缩的规定,并且引入更多审查程序。支持者认为此举可以更加好地保护原创者的权益,扭转他们被Google与YouTube等互联网巨头剥削的现状;然而更多反对的声音则认为新的修正案将加剧内容垄断,使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愈发不平等。

目前,博物馆与美术馆等机构也是发布在线内容的活跃主体,修正案的通过将怎么样影响他们的线上运营与规定令人好奇。虽然该修正案的实施与否依然取决于之后欧盟成员国的内部决定,但能够肯定它将对当代知识与艺术的生产及传播生态造成难以忽视的影响。从博物馆的历史上来看,版权一向是馆方在日常运营中相当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禁止观众随意摄影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篇旧文梳理了一些相关的史料,以期更全面地回答一个常常令我们感到懊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拍照?”。

观察公共博物馆在历史上出台过的大部分摄影规则,保护版权无一例外是馆方首要的着眼点。照相机在当下的廉价与便携性(例如手机相机)似乎让拍照成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下意识行为。事实上观众能否在馆内随意摄影是自摄影技术诞生起就被持续争论的话题。一方面博物馆利用摄影对于书籍、藏品或展示细节的还原度,出版了大量图录,使得知识与艺术能够在某一些程度上摆脱地点与阶级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另一方面,出版物与文创产品的贩卖也是博物馆维持机构运营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对于观众或第三方摄影需要报以特别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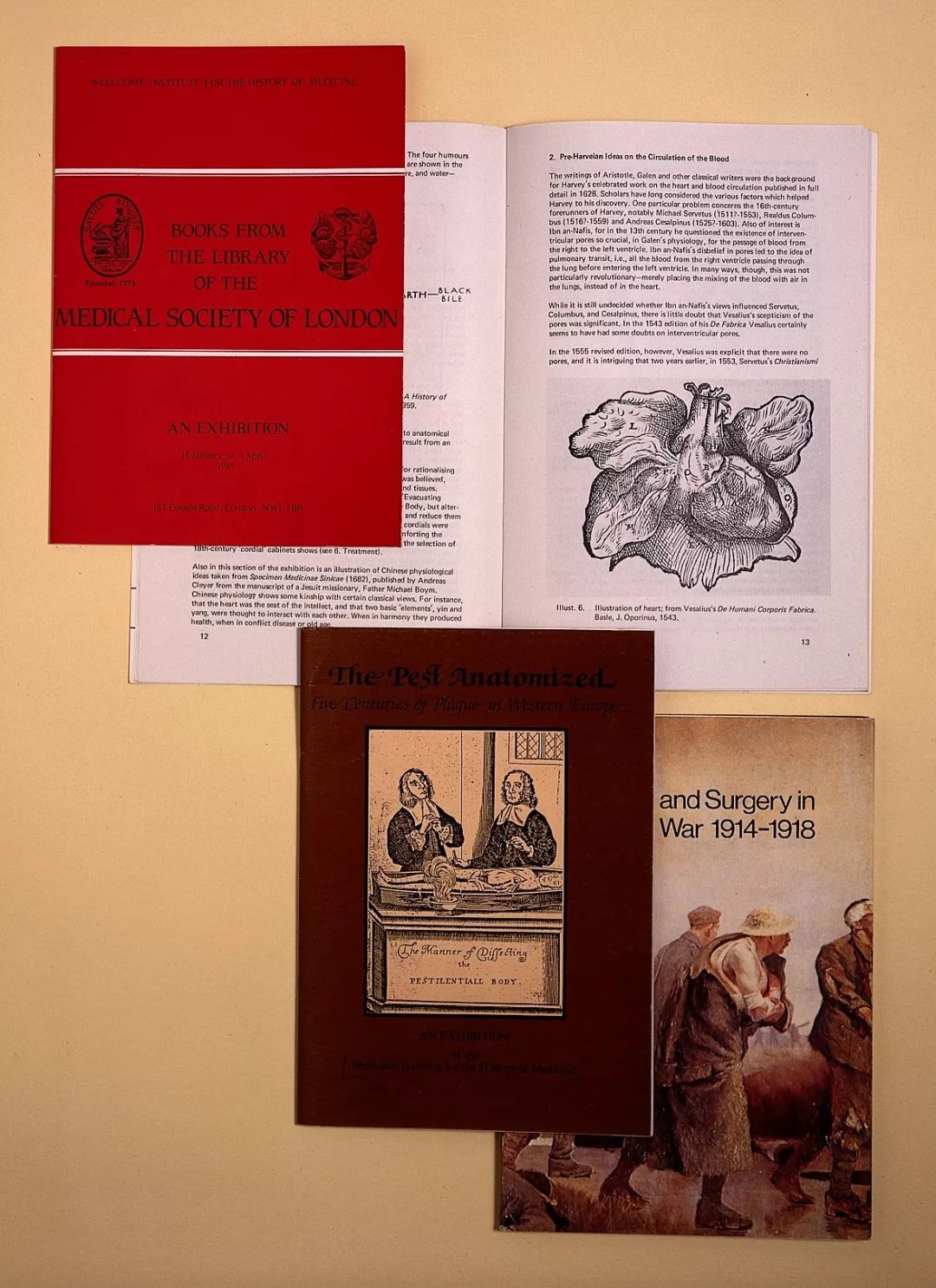
“公众可以付费查阅一部分古希腊手稿……这些手稿正在被制成铜板,然后印刷出版……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忙着制作我们收藏的绘画的铜板,因为国王决定尽快出版第一卷图录……据我所知,我跟你提到的这些是哲学手稿,但是我不被允许在信中更详细地描述它们。它们即将出版,届时我会尽快寄给您……”1
收取费用以此出让部分知识的可见性,是版权与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在19世纪摄影技术问世以后,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并且与资本主义市场越来越紧密地粘合在一起。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在《绘画与摄影》一文中记载,19世纪下半叶,法国政府曾将复制卢浮宫艺术收藏的独占权利转让给职业摄影师安德鲁·迪斯德里(André‐Adolphe‐Eugène Disdèri)。这种权利转让类似于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许几家文化创意公司使用其藏品内容生产商品并进行销售与营利的行为。20世纪初《申报》所载的一则广告可从侧面证明:
英國雲錦五彩石印公司(分公司在上海黄浦灘一號)近爲本埠某保險公司代印一種月份牌,精美無比,足爲印刷界放一異彩。其畫圖原係絹本中繪仙境人物,爲明代名家手。題口床世天堂,是圖向庋於英國博物院,兹由該印刷所得博物院之特許,用照相法拍出,製成銅版,以三色付印。較之原圖,毫無改據。言凡係中國古今書畫,均可代印云。2

除了对外版权协议,历史上博物馆也曾对“散客”收费。1906年,原先能够免费摄影的大英博物馆开始执行新规,规定在博物馆内摄影者,需为一张底片支付两先令的费用;或对携带摄影器材参观的观众,按照每小时一先令的标准收费。伦敦当地的出版商为此致信《》表达抗议,信中声称“出版商作为与此事关系最大的群体,有权对这项因使用公共财产而要缴纳的费用提出申诉”。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世界博览会中采取这种“措施”:据冯自由记载,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即规定“凡携带摄影器入场者,每具缴公费银二毫五分。” 这些举措似乎已经在现代博物馆中消失,不过让我们再思考一下石窟寺中常常设置的“特窟”,对于可见性的标价似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1915年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会馆旧照 图片来源于wiki common
近代诞生的版权法带有与生俱来的悖论,一方面它并不是为了提供一种特殊的私人利益而存在的,它强调个体的知识生产与艺术创作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版权为知识生产与艺术创作者提供继续创作和传播的经济激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自由市场,使他们获得独立于政府的经济保障。经济独立不仅仅可以保护原创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公共领域对政府或别的形式权力的监督。在这一层面上,许多在世艺术家的展览禁止观众摄影是一种必要的保护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版权法产生的诸多限制无疑不利于知识在更大范围中的传播与持续创新。对于博物馆来说,禁止摄影的背后需要仔细考虑的不仅是版权自身的矛盾,因其作为以保存人类文明与遗存为使命的公共机构,利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营利(即便不以营利为目的)能否自圆其说?
除开版权,我国博物馆在“禁止摄影”这一规定上还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其出发点在于对西方殖民者加注于我们的“凝视”感到异常反感。罗兰·巴特曾说,“奇特这一要素得以使我觉得摄影有存在的价值。反过来,没有奇特性,也就没有照片。” 摄影追寻奇特事物的天然属性,不仅在以远东地区为写真对象的早期摄影实践中一览无遗,同时也与西方早期博物馆对他文化的收藏与展示理念不谋而合。民国成立后,仅《申报》就发布过数次“禁止外人在内地摄影”与“限制摄影决定办法”通知。1930年《公安旬刊》刊发《故宫博物院禁止摄影》一文,时任院长易培基在所呈文书中写到:
為呈請事,籍查故宮所藏金石字畫各種物品,於歷史文化均有重要之關係,現在以次攝照,廣為流傳。惟此項物品,出自歷代祕藏,與普通照張不同,誠恐中西攝影家輾轉複製,漸失其眞,反與歷史固有之文化有礙。茲為保存古物眞相起見,特請令飭內政部准予立案,凡蓋有本院圖章之各種照片,一律禁止翻制,以重公物,是為公便,謹呈行政院院長謹。9
以精确复制见长的摄影技术,如何会在“辗转”中“渐失其真”,损害古物“真相”?今日来看以此作为禁止摄影的理由,自然是站不住脚的。然晚清以降,民族主义席卷中国,尤以知识分子对中国外在的形象很敏感。加之当时报刊的印刷质量低下,发行的摄影作品往往色彩失真,尺寸大小有限,给观者的印象与客观现实总有距离,因而易培基的担忧在其时不无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摄影问题依然相当敏感。1975年,国家文物局与外交部发布《国家文物局、外交部关于外国人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照相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表示许多外国人在参观国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时,系统地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样使一些“在国内因印刷条件”还未发表的重要文物资料,在国外却抢先出版,对出版工作非常不利。因此通知要求各文保单位与博物馆在参观前通知观众,石窟寺、古建筑等不能系统地照相(可以规定只许拍摄数张),还未发表过的“壁画、雕塑、博物馆陈列室内文物展品和馆藏文物,按国际上一般惯例也不能照相”。事实上,除外国人外,许多石窟寺与古建筑至今也未向公众开放拍照。改革开放后,国家文物局再次针对外国人摄影问题下发新的通知,名为《国家文物局对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摄影问题的规定第二项具体说明》:
经请示中央宣传部同意,我局根据中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中发〔1979〕15号)印发的《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摄影问题的规定》,对其中第二项具体说明如下:
一、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展品,已发表过照片的,可以允许拍照。为保护我出版权益,未发表过的,不准外国人拍照。凡不准拍照的文物,应在文物前标志“请勿照相”的中外文说明。
二、拍摄壁画、字画、纺织品等,不准使用强光灯(如碘钨灯),以免损伤文物。
三、非开放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需经国家文物局征求相关的单位意见,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方可允许外国人照相。
当时两份文件的执行情况,可由1980年《》刊发的一篇中国游记得到证明。作者在文中写到,中国大多数博物馆与古迹均禁止拍照,游览之处,唯有郑州市博物馆允许外国游客摄影。12
200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条款详细的《文物拍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已申明于2016年起废止,但暂未有相关替代文件发布),《办法》主要是针对产出高质量图像的专业摄影,包括学者研究所需摄影、电视节目与纪录片摄制、高清画册摄制等,此类摄影需报文物管理部门审批,向博物馆及文保单位支付一定的合理费用,并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其中第十六条规定:
对公众开放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公开展出的文物,除因文物保护的特殊需要而另有专门规定及说明者外,参观者可以拍照留念。但参观者不得以收集资料为目的对文物进行系统拍摄,如有需要,应参照本办法执行。13
《办法》的发行可看作是博物馆及其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对于新时代形势的适应,强调摄影涉及的知识产权与文物保护问题,同时也注意到参观者携便携式相机合影留念的普遍需求。据非权威数据,2003年国内数码相机保有量为110万台,2004年底为380万台,2006年这一数字为700万台。虽然数据存疑,但进入新世纪后,数码相机增速极快是不争的事实。
2006年,《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在展览上要接近群众,在服务上要贴近群众》,批评我国博物馆不分情况,一概“禁止拍照”的规定不合理,“保护知识产权与文物安全”只是借口,其实就是国内博物馆缺乏对观众的服务意识。《中国青年报》当年也发表社评《博物馆“禁止拍照”,不合理!!?》,文章还提到即使有“禁止拍照”的标识,大部分观众也会在自己认为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偷几张作为留念。自2006年起,观众拍照在我国博物馆中逐渐解禁,并逐渐形成“除馆方特别声明外,观众可以在参观时拍照,但禁止使用三脚架与闪光灯”的惯例。
近年来除了部分古建筑、石窟,我国大部分公共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拍照政策已经较为成熟与稳定。然而有趣的是,观众对此事的评论却在近几年内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究其原因,我国博物馆转型带来的观众人数迅猛增长是客观条件,基于社交网络展开的公共讨论所促成的观众共同体(community)则可视为由人数量变发展而来的质变。不妨观察最近几次拍照问题引起大范围讨论的起因:
2010年,奥赛美术馆馆长公开发表言论,称在美术馆内拍照“简直是野蛮行为!”引发诸多观众在其官方网站留言抗议,有观众不无讽刺地建议博物馆以后在每个作品前面都放一个箱子,观众要投一法郎才能在这幅作品前观看几分钟;还有人质疑博物馆禁止拍照仅仅是想增加官方明信片和图录的销量。
2015年,法国文化部部长佩勒兰(Fleur Pellerin)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两张于奥赛博物馆内拍摄的艺术品照片,引发网友大面积抗议美术馆制定双重标准,奥赛美术馆紧急决定修改其拍照规定,改为允许普通观众观展时的私人摄影行为。
2013-2015年间,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两次修改其拍照规定。第一次是由于许多观众反映博物馆禁止摄影的作法过于精英化,不够亲民;第二次则是由于开放拍照后,更多的观众反映在展厅内拍照的观众极度影响了其他希望安静欣赏杰作的观众,因此馆方再次禁止在参观时拍照。
201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中国:镜花水月》舞会,诸多名流在中国元代壁画前开闪光灯留影,引发国内舆论谴责。亚洲部主任向媒体解释大都会博物馆在日常展览中为保护壁画所作的努力,希望平息争议,然而收效甚微。

2015年法国文化部长在Instagram账号发布在奥赛博物馆摄制的照片 引发大规模抗议 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此可见,当代观众在拍照这一问题上,对于“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与“精英取向”相当敏感,并尝试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冲击由精英控制的传统参观秩序。例如在摄影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观众可通过抗议等方式,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左右馆方对拍照规则的决定;大量喜爱在馆内摄影的观众的出现,直接促成了各大博物馆在社交网络上举办各类“最美”活动,以扩展年轻观众;沉迷拍照的观众又迫使策展人放弃以枯燥的编年史式说教来策划展览的理念,转而以“能否让观众放下手机”为目标重新安排展览方式、空间和动线。因此,虽然有关摄影的争议暴露出业界与当代文化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但从积极的方面观察,我国博物馆观众近年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态集结,通过媒体与社交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博物馆公共性大幅度的提高的表现。
这篇推送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篇幅所限,也因为所有的领域对于闪光灯与文物保护问题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因而暂且不表。在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上,观众的声音常常很难追寻,但是有关禁止拍照的问题果然还是吸引了众多“吐槽”。1946年,施南池先生在《申报》发表《艺术品的复制问题》一文,公开批评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禁止摄影,其中一段说到:
最近大公報載,北平故宮博物院古畫一百幅,在成都舉行展覽,特別鄭重地宣吿:「展覽期中禁止拍照與臨摹」。這是什麼理由?國家收藏的古畫,爲什麽不准國人的「拍照與臨摹」?拍照與臨摹,無非是闡揚國粹與研究藝術;歐美的美術館,都是公開展覽任人臨摹的,爲什麽我們故宮博物院對此攝影和臨摹,懸爲禁例?試問這數百年以至千餘年的古畫,倘不公開任人臨摹,從事複製,那末,再數百年以至千餘年以後,故宮博物院用什麽科學方法永久保藏下去?担保牠不致自然毁滅?16

[3] [德]瓦尔特·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M]. 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2,137
《印刷工藝之異彩》.《申报(上海版)》,1916—03—03(3).标点符号为笔者加注。
冯自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见陈占彪编,梁启超等著.《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0:294.
[5] 尤杰.在私有与共享之间:对版权与表达权之争的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26-27
[6] [法]罗兰·巴特.明室[M].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9.
原文《“禁止摄影”:由观众拍照观察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发表于《东方考古》第15集